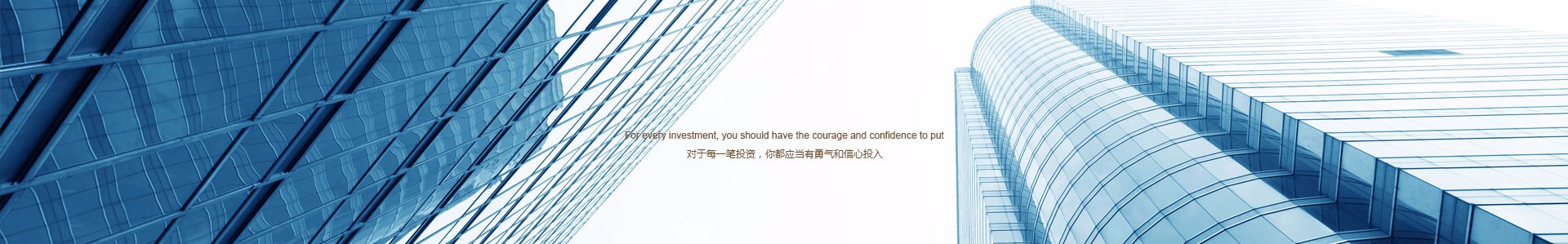对话王石:从哥本哈根到“生物圈3号”一切都不确定但你得准备着百家乐- 百家乐官方网站- APP下载
2025-10-11百家乐,百家乐官方网站,百家乐APP下载,百家乐游戏平台

你能想象吗?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这位曾叱咤中国地产江湖的风云人物,曾以硬朗霸气的特质让人印象深刻,如今面对公众,他却呈现出更多细腻温情和柔软的一面。
2025年9月6日上午,万科集团创始人、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深石集团创始人王石在深圳前海国际人才创新交流中心接受了华夏公益会客厅专访,端坐于镜头前的王石身材依然瘦削,白色立领衬衫质地精良,深色裤子加黑色皮鞋,清爽又不失品位。采访中,王石就万科公益基金会社会化发展思路、持续助力政府打造碳中和社区,以及如何通过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将企业家精神构建得更为完满等诸多问题阐述了观点。
而就在前一天,9月5日“中华慈善日”,《王石:善行万里,归来还是企业家》研究报告由《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在深圳发布。报告称,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王石在二十多年间以“超级志工”的身份参与发起了阿拉善SEE、壹基金、深圳红树林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西安市乡村发展基金会等近50个社会组织,深度参与28个机构的决策与管理。报告统计,在其任职期间,其中有10家基金会公益支出累计超过41.7亿元。
2017年6月30日,王石正式辞任万科董事会主席,并于不久后就任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此后,逐渐褪去万科烙印的他,公开表示“年轻时追求事业高度,现在更珍惜与家人共度的平凡时光”。与此同时,他志趣的重心更着眼于公益慈善事业,倾力推动万科公益基金会专业提升,打造“可持续社区”,在倡导绿色环保社会共识等方面更是不遗余力。
2021年,依托我国发布的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王石开创了告别万科后的第一个项目“生物圈3号”。
王石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按实际估算,这些年他参与过的公益组织接近100家,但时间精力有限,他参与的形式和程度也有所不同——多花时间、专注投入是一种;弹性参与,例会出席是另一种;再就是挂名——他会对挂名的机构是否“靠谱”预先评估,再做决定。他算了笔时间账,“50家社会组织一家给一天,50天就快占到年均1/7的时间了。人情世故难以避免,调配好还过得去;调配不好就处理不好——那是你自己的问题。”王石笑道。
当《华夏时报》记者问起如何看待企业采用公益营销方式拉近与消费者距离、提升品牌美誉度的做法,王石说“这个问题还真没深入思考过,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但他又说:“现在一些企业搞促销,一杯奶茶里有5分钱就是做公益,年轻人买账。”
说起万科公益基金会通过丰富多元的互动方式与社区居民建立联系,动员和引导他们参与社区减碳,王石举了好几个真实生动的例子。比如,被幼儿园小朋友带动家长做起来的二手手机回收再利用的“绿盒子行动”,比如联动社区跑步小组或老年合唱团一起参与社区生态环保建设。他认为,“用心组织,慢慢推进,持续倡导,再难也会有收获。”王石指出,企业家做公益是本分,“有心”非常重要,因为企业家“本身就有这个担当”。如果企业家除了铆着劲赚钱,其他一切都不管不顾,长此以往,不仅自身发展不平衡,社会也要失衡。
对已经推进四年的创业项目“生物圈3号”,王石谈兴盎然。他不讳言,如今面对的所有知识都全新且不乏挑战,但这似乎更是一种生命能量的正向加持,他觉得这件事辛苦但更有趣:“恶补专业知识是肯定的,我从来都没有停止学习。”
《华夏时报》记者追忆5年前在亚布力论坛专访王石,说那时的他不苟言笑,过于严肃,而此刻的他要松弛亲和得多。王石当即笑起来,称自己第二次创业之后整个人变化很大,一点儿也不焦虑,更踏实和从容,因为人生行至此处,他早已看淡许多。如果说除了推进创业项目发展还有什么事可以让他一边欢喜期待,一边认线岁再登珠峰的计划,因为“人生无常,要少留遗憾。”
专访拍摄结束,王石主动邀请两位摄像师合影留念。镜头中,他的笑容温和平静,充满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豁达与释然。
《华夏时报》:欢迎王石理事长做客华夏公益会客厅。印象中您曾说万科公益基金会成立到现在,从早期公益项目的个人色彩到致力于打造社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打造碳中和社区,向社会化基金会迈进。在您看来,达成这个目标,万科公益基金会可能还要积累哪些必备的特质或者说是基础来完成它?
王石:所谓“社会化基金会”,是我当时创办万科公益基金会的一个理想,现在应该还在转化过程中。虽然它的社会贡献力、影响力不错,但如何能把它做成真正有影响的基金会并不容易。不能说这是中国有名的基金会,而在国际上大家不知道你,所以这个社会化的转化应该从国际化才算开始。第二,公益基金会做环保,重点是设计的环保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但如何做到标准化,现在还在形成过程中,做公益也需要产品标准化,才更适合推广和扩大影响。
《华夏时报》:您觉得作为一个基金会来说,对于社区居民打造碳中和社区、包括日常垃圾分类、环保等方面常识的养成,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推动?
王石:万科公益基金会现在做社区环保生态,我个人认知,就是关注环境如何循环可再利用。这样的观念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有的,我们叫“天人合一”,那就一定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相生相融。怎么组织他们?这个过程知易行难。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原来垃圾都不分类,即使你分类,垃圾车来又给你混在一块收走了,没有分类垃圾车。这时候就把小区居民动员起来,他们愿意分类分拣。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居民,是物业管理,他们说“我们做了没用”。我跟公益基金会的小伙伴们说:“看似没用,我们也要做。”
意义在什么地方?——第一,尽管最后这个结果没有再分类、可循环再利用,但分类本身让居民养成了习惯。第二,分类出来的瓶瓶罐罐,物业管理可以联系废品收购站,人家专门来收购,虽然钱不多,也是循环再利用,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在万科的小区推广这些活动,第一个响应且被感动的是广州白云区,白云区委书记对所在的三个万科的小区做了垃圾分类,即便就是这三个小区,也有推动促进作用。可能是很难,但这是不是代表未来?当然是。
《华夏时报》:现在国内很多企业都有自己的基金会。您认为一个企业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王石: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成立基金会,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现在比较流行的叫“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就不仅仅是关心企业股东利益和企业员工利益,还关心与其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甚至不相关的利益。可能你要问的是,企业做的公益往往是和企业本身相关的,那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局限性又在什么地方?
一般企业做和自己相关的公益,我个人觉得这是最好入手的。举个简单例子,比如保险公司做公益保护古树。保险公司给这个古树做保险,不是直接拿钱,是万一古树出了问题,我给你赔。我认为他给的保险价值,比他给同样一笔钱的价值更大。
王石:至于说局限性,企业会自己来对标和扩充这个边界。我个人觉得,更多是从积极意义上看这个事。
《华夏时报》:说到企业家做公益,您提出这么一个观点,说“如果不做慈善,企业家的精神不是全面的,甚至他的企业家品格会缺那么一块。”我采访过的大多企业家,有一个基本价值共识,“作为企业家,我做好自己的企业,带好自己的员工,依法依规向国家纳税,在做好这些已经很不容易的基础上,还要赋予我做公益慈善的社会责任,这对我来说是不是太难了?”您提出的这样一个标准,对企业家群体来说,是不是有一点苛刻?
王石:合法纳税、解决就业、创造利润、创造社会财富,那叫“本职工作”、叫“本分”。你作为一个企业家,这方面你做得非常优秀,和做公益慈善是不等同的,不是说我交税了,创造利润了,给股东赚钱了,就是最大的公益,这个概念是模糊的、是混淆的。
过去基本上什么事情政府都给你考虑好,包揽了,公益慈善也是政府都做好了。只是逢大灾大难之年,突然应付不过来、紧急调配不回来,才需要老百姓、需要做企业的来捐钱。现在应该反思,面对未来的现代社会,企业要扮演什么角色呢?应该说扮演两个不可或缺的角色:第一,企业是要出钱的。平时防患于未然就最好。比如不要最后发现很多留守儿童没人管教、形成社会问题了,你才去做、去应急。第二,企业是要出力的,不是干体力活,是企业家的创新。
《华夏时报》:如果咱们把公益慈善这部分的担当、热情和奉献补上。对于企业家来说,人格魅力也罢,作为企业带头人也罢,都是他的工作动能会更饱满、可持续发展会更有后劲?
王石:这是个角度问题。至少我觉得我是这样,但不能要求别人都像我这样。他遵纪守法,又能盈利、又能解决就业,其产品社会也能接受,那也挺好啊!但从一个企业更长远的发展来讲,这个缺失(公益事业)越早补上越好。
《华夏时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说有些企业觉得做公益成了负担,或者说有点不自愿的情况下被迫去做,可能效果也不好。
王石:这是自愿原则、自我选择,它不是法律规定,所以也要警惕另外一种情况,叫“逼捐”。
《华夏时报》:大家很关心这个社会议题——一个社会的公共精神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个社会国民整体的精神素养?您认为公益组织的存在是拾遗补缺的一种形式,还是社会主流价值观背后的隐形推手?
王石:它应该是显形的主要推手,不是隐形推手。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的进步,企业家毫无疑问已经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了。但NGO这种公益慈善组织扮演的角色,现在才开始。改革开放这第二个40年,应该是中国NGO组织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是拾遗补缺,而是非常重要,至少占到20%到25%。
《华夏时报》:2009年,您代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参加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现在是第16年了。2013年您提出要设立“中国企业家日”,大会也欣然采纳。在这样的国际场景下,您提出这个建议、包括后来有这样的成就,对于中国企业家群体来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含义和社会价值?
王石:2013年,我们作为赞助支持方建设这个馆,中国政府代表团就给了一天时间,以“万科企业日”命名授权,我没有用“万科”两个字,采用了“中国角企业日”,因为这个平台是号召更多的中国企业家组织来参加,(这种核心精神)从2013年一直贯彻到现在。(2021年)我们独立建了馆,就叫“中国企业馆”。
2009年参加的时候,组织的那个团一共就三个人。一个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还有两位企业家,我是其中一位。那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别人看我们很陌生,我们看这个环境也很陌生。到了2015年那年的会议上发生很大变化,代表团有(17个行业),去了90多名(企业家),代表将近10万家中国企业。再到第24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代表中国各行业的企业家和高管100万人次。
王石:指数级增长,这个真是不得了!光这样一个数字,在国际上已经非常大的反响。但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企业呢?超过4,000万家,(代表)100万人次也不多。既然如此,那咱就不要求数量,要求质量。
《华夏时报》:现在很多企业都有自己的ESG报告。有业界人士说,目前按照ESG治理要求达标的企业,其实寥寥无几,但大家都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您的观感是什么?
王石:ESG它不仅仅是气候变化,还涉及男女平权、少数民族、等等。世界500强企业,几乎100%都有ESG报告。在中国,已经上市的和准备上市的企业都有要求,必须要有ESG报告。我个人认为,有要求比没要求好,因为中国文化更多是自上而下,更多要企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有比没有更有积极意义,这跟思维方式有关系——你不要求他,他就觉得我不应该做,主动披露的会很少。
《华夏时报》:2021年,您再次迈开了创业步伐,这次您聚焦碳中和,包括可持续发展这个大的领域。为什么?
王石:万科绿色低碳做得非常好。从2000年成立建筑研究中心时,万科就开始研究装配式住宅、搞绿色低碳,到我决定再创业,已经20年了。2020年中国宣布双碳路线碳中和。我一听立刻就觉得,这事我要做,不做都对不起我自己。
《华夏时报》:您是一个喜欢迎难而上的人,还是早有准备、只等时机的一个人?
王石:我不是早有准备,只能说是否时机来了,我必须得做这个事了,只能说一不小心,我准备了20年。我认为做企业三个层次:第一毫无疑问是做产品,第二做品牌,第三做标准。最高境界是做标准。我的“野心”是什么呢?ESG住宅产业要做成标准化。现在是碳中和经济时代,碳中和一定是要商业化的,不商业化钱远远不够。中国已经公布了双碳路线图,我一定要有用武之地。
王石:不是说我有信心做不做标准。首先,创业第一个要素是你能不能把它打造成商业模型,非常清楚。ESG不是商业模型,它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作为一个企业家,你觉得能不能成?我当然觉得成。但是你成不成,不是你觉得成不成,而是要靠最后的实践、靠产品能不能被社会接受。
2020年我决定创业,线年开始,今年是第四个年头。我做的第一个项目叫“生物圈3号”,各种运作探索,当然不容易,但做得兴致勃勃。也有很多我的老部下、老朋友替我担心,说“你这个年纪了,本来是搞房地产的,现在你搞碳中和,牵扯到新能源、新材料和大数据,这些对你来讲都是陌生的。你不要以为搞房地产成功了、做公益慈善很成功,你做了我们这行也能成功”。
《华夏时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会恶补对您来说陌生的,甚至比较晦涩的一些知识吗?
王石:对我来讲,一个企业家做公益是分内的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钱没力,捧个人场。我很想借用中国一句古话“予人玫瑰,手有余香”,你赠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获得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你同时也得到了回报。
《华夏时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个是比较文绉绉的说法。我觉得可能您刚才这句话传递的信号是:“善有善报”。
《华夏时报》:我们给别人更多的付出,他可能不会在同一时点回馈给你,但也许在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给到你。
王石:是这样。你不乞求他的回报,那就是水平更高。但你有需要,他突然给你,那是不是就是意外的惊喜?
《华夏时报》:在这些时点当中,您会不会某一个瞬间会觉得有一点勉为其难,或者说心里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王石:没有什么不舒服。如果有什么不舒服,就是(被动的)人情。有时你会觉得,怎么是这样——你赠予了,很多人认为你应该,你不给的时候,他就非常抱怨你。
《华夏时报》:是不是您原来的给予,没有把握好度,施予过了的时候,反而形成一个很不好的互动,让自己被动了。
《华夏时报》:人生行至此处,您对自己过往的生命轨迹,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和总结?
王石:1983年,我从广州辞去公职到深圳创业,一不小心就成为一个企业家。当时就想,既然是经济大潮、改革开放,做生意赚点钱就出国进修,再做其他的。我小时候有很多梦想,但没有一个梦想是我会成为一个商人、成为一个企业家,但大丈夫志在四方、要做出一番事业,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王石:当然很多啊!比如说我喜欢读侦探小说,美国有一个华人神探李昌钰,我幻想成为中国的李昌钰。还有狄仁杰断案,这些我都非常喜欢。也想成为外科医生、想成为战地记者、想成为小说家,还非常喜欢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还有探险。
50岁的时候,结合我自己的能力和社会对我的认知,我知道,我只能做一个工商业从业者、做一个企业家。50岁我才给自己这个定位。定位了,并不等于安心,只是知道你也不可能再转行了。
王石:此生就是它了。实际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看不起商人,既然你是(商人)了,你还看不起吗?那咱们怎么想办法看得起自己呢?你是不是得从自己做起?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怎么让别人看得起你?这样的认知过程一直到现在。我是过来人,年龄也比较大,在这个阶层当中多少还有点社会影响力,也非常愿意把自己认知过程的变化和大家一块来分享,让我们共同看得起自己。
王石:就是要自我救赎,你要自己认识自己。是不是商人全是这样?也不是。我们再一挖掘对比,很惊讶地发现:从20年代到现在过来的工商业者,他们的认知和水平,我们现在远远不如。很重要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是他们最基本的教育和认知。我们这代人过去都是自修,没有更系统的训练,如何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我们是模糊的。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代商人的问题,包括各行各业都差不多。2011年那年我都60岁了,我去哈佛做访问学者,在重新学习的过程当中,认知一些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你对你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怎么比较?慢慢认知自己哪些东西是好的,我们要继承;哪些确实也有不好的、我们血液里根深蒂固的、你想扔都扔不掉的,那你要警惕。现在是不是一切都拿来主义?看来不是的,它有它的局限性。
王石:现在我就感到,有这样的历练和这样的经历之后,再重新创业,我是很安定的,我一点也不焦虑。
王石:那当然是,中国现在不就缺少这种从容吗?一切都在焦虑,一点都不确定。我非常清楚,我也知道,哪有可为,哪有不可为。
《华夏时报》:现在很多人觉得有车有房有豪宅、有足够的财富就是成功的标准。那您的成功标准是基于什么样的界定——当然,这些(世俗之物)您都有了!
王石:我没有。(笑)我没有定一个什么标准,对我来讲,是现在我要警惕的是什么。
王石:嗯,尤其是60岁之后,我要警惕的是,我还有没有好奇心。对我来讲,只要你还有好奇心,你的生命还在成长,还有增长的空间。我就希望我的增长期时间更长一点。
王石:刚才你说怎么界定成功的标准,那就是你在社会上有没有价值。所谓“价值”,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你能创造财富、能挣钱,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到一定程度,你不但要挣钱,是不是还可以在这些社会组织当中扮演角色,这恰好是我非常在乎的。第三,你已经是过来人,你还希望你创造的社会财富是真正可延续的、是一代一代的传承。我觉得我这个年龄,我的经历有资格这样去说了,会更多鼓励和引导年轻一代去做。
人生不过百年,是不是到80岁、90岁还能很健康,并且不成为社会的负担,对我来讲,我更在乎这个。所以为什么把目标定到81岁我再去登珠峰呢,就是这个意思。
王石:(笑)我什么时候吹过牛?你看我这状态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再有六年(81岁)。
王石:积极的心态!人生不过百年,我非常明确、我非常愿意安乐死,不要在ICU插喉管,抢救得生不如死,亲人受煎熬,财富被浪费。一定要坦然面对死亡。
王石:关于死亡,我从来不忌讳。你再不谈,(假如)明天你就走了,这不是人生大遗憾?
《华夏时报》:跟您的聊天,让我想起了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一句话,“人生是不可以被打败的,你可以毁灭它,但你不可以打败它”,您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种精神特质?
王石:我们其实也有很脆弱的时候,不过我现在表现没被打败,这是侥幸而已,是人都会有脆弱。
《华夏时报》:我这次采访您,跟5年前亚布力论坛采访您相比,您更松弛、更从容,也更有亲和力。
王石:那当然,我太有感觉了。原来到了某一个城市、某一个省,那里领导请我吃饭,我说我没时间。现在,街道办事处主任请我吃饭,我都有时间。(笑)我在创业、我在搞碳中和社区。
《华夏时报》:我觉得特别好。我感觉您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乐观主义者,就是在行动中去克服困难。
王石:我变化非常大,原来非常自我。古希腊阿波罗德尔斐神庙有一句话叫“认知自己”,世界上最难的就是认知自己。
《华夏时报》:感谢您接受华夏公益会客厅专访,也衷心祝福您81岁再登珠峰这个目标能够早日实现。